熗漿水
高德恩
搟好的兩片面晾在上房腳地和案子上。媽媽在墻角棗樹下的蔭涼中摘父親鋤包谷時挖的小蒜,做熗漿水的準備。全家的銀行,一白一黑兩只母雞和一只棗紅雞公在媽媽身旁翻尋吃食,并時不時咕咕咕叫二聲。那是我們家針頭線腦,稱鹽打醋,買祭祖用品和我的學費的唯一來源。魯迅于散文《秋夜》篇首寫道“:在我的后園,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,一株是棗樹,還有一株也是棗樹。”此處的描寫,寄蘊的是作家心中的愁悶、憂憤和“我以我血薦軒轅”的誓死不二。而我們家的棗樹,則是每年秋季打下棗子,賣三塊五元貼補家用的,或給我換回愛讀的《唐詩三百首》和連環畫等。
媽媽將切好的小蒜段段置切刀上放在鍋邊,給灶膛中添把蒿柴,提起掛黑釉的葫蘆瓶,湊向鍋邊,拔出油浸透的木塞塞,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似往偌大的鍋里滴下三、四滴葫蔴油或菜籽油,又咬牙從那軟木塞塞上捏出一、二滴。嗞……油香味令我饞涎欲滴,食欲暴長。繼之,媽媽嫻熟的將半瓦盆以性寒味苦,補臟利膽的苦苣(敗醬草)為食材,發酵成的漿水酸菜傾倒鍋里,放鹽、溫熱舀出。待會兒舀二勺澆于煮熟撈碗里的面條中便為改善生活。日出月沒,斗轉星移。直至今日,我才明白,滴入鍋中的那幾滴油,高溫下已變成噴噴香的味兒變成氣體飄拂了。小蒜于熱熱的干鍋上一?黃,漿水嗞的涮凈了鍋底殘存的油沫沫。給予一家老少十人的則是心里慰藉:我們家今天吃熗漿水長面了。父親也會藉此吃飯時對我說三、四天,德恩,想天天吃熗漿水的長面,就要好好學習,走出這窮窩窩!誠然,真要在那漿水中覓得一二油花花,根本就是意念中的奢想而已。多年前在什么地方看過一首周文王詠漿水面條的詩,只記住了尾聯“竹籬茅舍酬親友,漿水面條味最長”二句。周文王姬昌訪姜子牙于渭水之濱,應該到過天水。且在卦臺山體悟過伏羲所畫先天八卦,為后來被商紂囚于今河南湯陰之羑里,將其演繹為六十四卦打牢了基礎。媽媽和眾多天水人相因相陳,百吃不厭的漿水面條,應該是對3000多年前周文王詩贊過,8300年前“人文始祖”伏羲率先民以大地灣為中心,由茹毛飲血,斷竹續竹向種植黍稷的農耕文明過渡中,所食漿水面條的傳承光大。讀已故作家、詩人王若冰贈《揮別大師》,書中一文記述,已故著名文藝評論家、散文家雷達,在天水參加完活動赴宴中就想吃一碗飄著紅辣椒絲、白蒜片、綠韭葉的漿水面條,但在家鄉終未如愿,留下了跨越陰陽兩界的遺憾。“故鄉在胃里。”鄉愁在舌尖上。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承就在吃穿住行,一頻一笑和相互的謙讓、包容中,而不在穿金戴銀,抖錢炫富上。文化藏于生活,富貴藏于文化。所以,《周易》六十四卦,最好的是謙卦,謙,尊而光。
白的蒜片,紅的辣椒絲躺在切菜板上,小碗中的炒韭菜的熱氣在減。世界衛生組織規定,一個人每天需要攝入25克食用油。而我熗一次漿水就能耗掉一人一天的食油量,更是媽媽熗漿水數月乃至半年的量。因為那黑釉葫蘆瓶只能裝一千克上下食用油,那可是我們全家十口人一年的奢侈。蒜片黃了,辣椒絲炸干了,我掇起漿水倒入鍋里,其不足兩碗中兀的汪實了一層油花花。“油太多了。”妻瞅著不銹鋼小盆中的漿水說道“:漿水面就吃個爽口清淡,下次一定少倒油。”我笑笑以示回答,下次依然我故。由奢入儉,的確不易。儉是淡的基礎,淡為儉的結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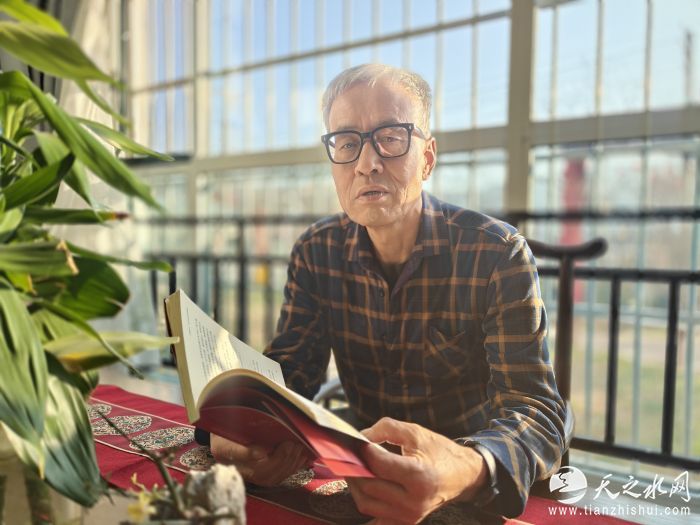
高德恩,字山行,甘肅天水人。2015年出版《高德恩詩選集》,系《中國書畫報》撰稿人、麥積山石窟藝研所特聘研究員。小說、散文見于《飛天》《朔方》《延河》《甘肅日報》《天水日報》等。以《文化成就的書法大家——吳善璋》《麥積山壁畫與中國畫的守正創新》《詮釋王羲之的以“意”為書》《玉壺盛春見美襟》《丁尚德——耄耋方顯韶華年》、《屈德洲——書如其人求和善》、《從黃賓虹80求脫談中國畫的守正創新》、小說評論<如果山丹丹皇后》是一面鏡子>及書畫評論和人物專訪刊發于《中國書畫報》《人民日報》、《中華新聞報》及《百度》《搜狐》《頭條》等門戶網站;中篇小說《分紅》、散文《買書》《熬臊子》《用照相機書寫生活的朱誠樸》等首發《天之水》網站,多家媒體轉發,獲好評。



已有0人發表了評論